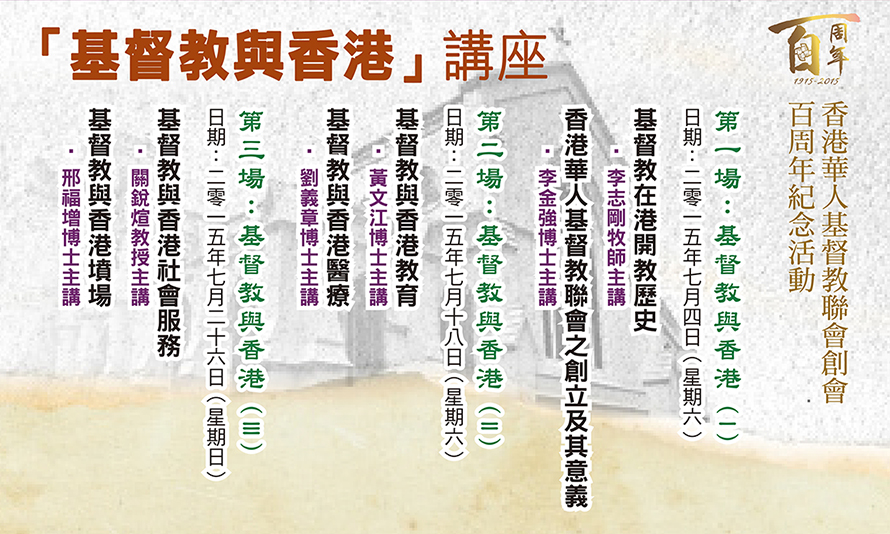論時代的邪惡
第 2971 期(2021 年 8 月 1 日)
◎ 每月眉批 ◎ 施德藩
「由於大部分邪惡的形態,都已經內置於我們各種社會系統之內,因此服務那些系統的個人,很可能對自己所做的事的嚴重性並不知覺。這並不是說他們只不過是歷史勢力的布偶。正如諾姆杭斯基(Noam Chomsky)曾經指出,一般來說,知識分子並不需要對權力說出真相,因為權力無論如何都知道真相。然而,就算是這樣,很多在政治上行為討厭的個人,其實都是有感情、滿有良知的男男女女。他們相信自己無私地服務國家、機構、上帝或自由世界的將來,而這一切,對於一些美國右翼分子來說,幾乎都是同義詞。這些人覺得,他們那些不體面的行為或許惹人討厭,卻是必須,就像間諜小說中的特工那樣。拔除其他人的指甲,並不是他們會在一個理想世界中選擇做的事。這也是其中一個原因,為甚麼那些拔除其他人指甲的,尤有甚者,是那些指示他們這樣做的人,仍然能夠侃侃而談道德價值而不感到太大的不協調。那些價值對他們來說可能是真確的,只不過它們在生意上或現實政治中佔據一個不同的範疇。而這些不同範疇之間,並不特別期望會有甚麼交叉重疊。正如一些犬儒評論說,當宗教開始打擾你的日常生活,也就是你該放棄它的時候。」
~Terry Eagleton, “On Evil”, pp.144-145, Yale University Press, 2010
對於邪惡,人們一般都以為只有窮凶極惡、喪心病狂的人,才會對其他人狠下毒手。因此他們需要受到社會的約束、法律的制裁。但妖魔般的行徑,並不需要衣冠禽獸去執行。情報機關的酷刑拷問者,毫無疑問是委身的丈夫和盡責的父親。而雖然我們常說「一將功成萬骨枯」,但軍事上的屠殺行為,很少能夠歸咎於個人。那些偷竊退休基金、污染一整片地域的,都是一些衣冠楚楚、溫文爾雅的斯文人,而他們往往只不過利用法例容許的漏洞,從中撈他一筆。如此而已。
這裏的重點是,大部分的邪惡,其實都是制度性的,依照既定的規矩和無私的程序。因此,好一大部分的惡行,都是源於平靜、體面、毫不咄咄逼人的動機,如怠惰、恐懼、貪婪和欲望。這些動機,往往被視為不道德多於邪惡。因此在絕大部分情況下,我們需要恐懼的,大概是老式的自私與貪婪,而不是邪惡。
另一個例子,是漢娜鄂蘭所謂的「平庸的邪惡」:負責屠殺千萬猶太人的艾希曼,並不是一位政治狂熱者;他只不過是一個極其平凡和平庸的公務員。他以陳腔濫調為自己辯護,完全沒有自己個人獨立的思考。事實上任何人放棄自己對是非善惡的判斷,而完全服膺於權威,那麼就是最平凡的人,也可以導致最極端的邪惡。
梅頓(Thomas Merton)曾經以他敏銳的時代觸覺指出:「這個富裕世界的人口,是孕育於野蠻神話與幻覺的穩定餵飼,被一個本質上暴力的生命,控制於一個恆常高張力的頻調中,脅逼着大部分人口,屈從於一種人性難以忍受的存在處境。由此而來的,是謀殺、強暴、犯罪、腐敗。然而必須記住,在貧民窟爆發的罪案,只不過是那更大、更普遍的暴力的結果:即最初逼使人們住入貧民窟的不公義。這樣,暴力的問題就不僅是幾個暴亂者的問題,而是整個社會結構的問題;這社會在外面井然有序、備受尊重,裏面卻充斥着病態的沈溺與妄想。」
然而信徒對於制度邪惡的忍受能力,卻往往顯得有點匪夷所思。我們的想法是:「那不能摧毀我的,將令我變得更加堅強。」於是我們嘗試打掉門牙帶血吞,相信一切最終對我們帶來益處。
但李察伯恩斯坦(Richard Bernstein)認為,在奧斯維辛之後,如果還繼續從一個「最終叫人得益」的角度去看待罪惡和苦難問題,可以被視為猥褻(obscene)。
其實就算在納粹集中營之前,嘗試從一個積極、正面的角度去看待罪惡和苦難問題,已經常常受到非議。不要說六百萬猶太人的身家、性命以及作為一個人的尊嚴;個人自由受到侵犯、財產被無故掠奪,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接受。
換句話說,不論上主對一個人的心意或計畫如何,如果我們看見他受到罪惡的暴虐和欺壓,在能力所及的情況下,周邊的人就有施以援手的道義責任。在當中,我們並沒有揣測上主心意的空間。意思是倘若上主要他在甚麼地方受到試驗或磨練,那是任何人都管不着的事情;但倘若我們遇上弟兄面對生死存亡的關頭、或被剝奪作為一個人的權利和尊嚴,那卻是我們無論如何推不掉的責任。
【要聞】
【教會、機構短訊】
【教會之聲】
- 繼往開來的培靈會 ◎ 翁傳鏗
【誠心所願】
- 誠心所願 ◎ 李鴻標
【釋經講道】
- 屬靈人的生活表現 ◎ 張天和
【咀嚼聖經】
- 挪亞的葡萄酒 ◎ 曉安
【城市心靈】
- 憶六四年東京世運會 ◎ 吳思源
【天地人和】
- 物種命名記 ◎ 文:方鈺鈞;圖:羅益奎
【平視人生】
- 仲夏夜之目 ◎ 李灝麟
【心靈絮語】
- 冤案和冤獄 ◎ 李碧如
【每月眉批】
- 論時代的邪惡 ◎ 施德藩
【牧心世情】
- 文化與防疫措施 ◎ 陸輝
【生命教育】
- 生命教育與全人教育 ◎ 龔立人
【畫出深情】
- 假如我失去視力 ◎ 黃葉仲萍
【福傳中華踏腳石】
- 歐陸首人郭士立 ◎ 區伯平
【譯經隨筆】
- 電子聖經庫(二) ◎ 洪放
【連載小說《捨得》】
- (五) 天上的淚 ◎ 寸草心